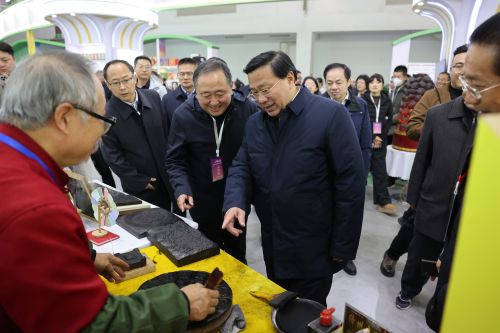饸饹面与红烧肉薄片、海带丝、酥肉片及各种佐料完美结合,每一口都香味十足
山西面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,因其繁多的面食种类,丰富的制面原料,独特的制面工艺,多样的制面工具等,体现出浓郁的百姓饮食特色,随着历史的积淀,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山西面食文化,也因此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组成部分里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的老家位于山西省中南部,汾水之滨——临汾霍州,霍州人爱吃的还要数饸饹面了,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、朋友来访必吃饸饹。
饸饹面是一道用料考究、独具特色,已有千年历史的风味小吃。饸饹在古代称之为“河漏”,元代农学家王祯在《农书·荞麦》节中有:“北方山后,诸郡多种,治去皮壳,磨而成面,或作汤饼(古时称汤面为汤饼),谓之河漏。”第一次出现了“河漏”一词。“河漏”这个名字比较特别,是如何来的呢?据说这与北齐开国皇帝高洋有关。高洋在太原称帝后,他儿子要过生日,便邀请王公大臣们来赴汤饼宴。汤饼制作费时费力,御厨便想了个办法,把面放于床洞上压,效果出奇的好。御厨用的“床”这个物件,不是我们现在睡觉的床,而是古代游牧民族使用的一种可以坐的家具,后传到中原地区,被叫做“胡床”。山西现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仍管凳子叫“床床”,这种叫法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。一开始,用这种“床”做出来的面叫“促律忽塔”,完全是根据压面时发出的声响而起的名。后来因架床于锅,如同面漏入河中,便叫了“河漏”,也有地方叫“河捞”。所谓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后来人们又发明改造了“河漏床”这种加工面食的专用工具,一直沿用至今。“河漏床”体现着山西劳动人民勤劳朴素的生活,他们用智慧不断提高他们的饮食境界。
饸饹虽是平常百姓家的日常食物,可它却并非无名小辈,那可是进入过御膳房的。据说,号称“千古一帝”的康熙就非常喜欢吃饸饹。有一次,康熙皇帝指派专人对全国风味小吃进行摸底统计,按图索骥寻找名吃时,点到了“河漏”,遂命人依法炮制,吃后赞不绝口。而当时正值水患严重,他曾六次南巡,亲自巡视黄河河道,督察河工,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,闻“河漏”一词心中深感不快,遂挥笔把“河漏”改为“饸饹”。至此,饸饹这一地方小吃便身价倍涨。

浇卤的师傅不紧不慢、一勺一碗地加臊子,臊子稠稠的、亮亮的

面块在夯木的按压下变成长长的饸饹,落入锅中,如蛟龙翻滚
从此以后,如果霍州人说“去某家吃饸饹”,那一定是这家人要“过事”了,“过事”就是办红白喜事,吃饸饹也就成了霍州人答礼吃请的传统。
霍州人每逢婚丧嫁娶或是乔迁请客就要一次性做十几斤的饸饹面。制作饸饹面一定要用好面。过去自家磨面时,人们往往会取最先磨出的面,这样面麩皮少,做出的面口感也更为筋道。我们当地的饸饹面是用饸饹床子压出来的,所以也叫“压饸饹”。一张饸饹床子有三尺多长、半尺宽、一尺高。床子看似简单,却也别致,整体由三部分组成,底部有一块三寸厚的托板;中间有一个直径三寸左右的圆孔槽,槽底有一块有孔的漏面铁片;上面是一个木头压手,压手中间是一个与托板上孔槽相匹配的圆形夯木,床子前有一个将托板和压手固定在一起的方形框架。这一“庞然大物”架在农家大锅上,那气势足够威风,因此并非家家都有。压饸饹那才叫热闹,在过去,饸饹床子多是枣木的,沉重而结实,稳稳地架在大锅之上。待锅中水沸腾,将饸饹床子上带孔的漏面铁片正对锅中央,在圆孔槽里放入一块儿大小适中的面,然后把夯木对准槽子慢慢地压下去,最好一气呵成。十几个小伙子或俯身压在饸饹杆上,或两手抱住杆子将身子悬起,或踩在由主杆再接长的木杆上。男人们不缺力气,矫健地爬上爬下。为首的一声吆喝,饸饹床就开始吱呀作响,面块在两三斤重的夯木按压下变成了长长的饸饹,落入锅中,宛如蛟龙翻滚,甚是气派。饸饹压出来后,第一窝饸饹自然被称为“头窝饸饹”,其意义不同寻常。当地人办喜事时,通常会将“头窝饸饹”专门留给新郎或新娘食用,寓意新婚夫妇,一生一世,长长久久。

五花肉炖得软烂,卤汁的酱香味喷薄而出,这一碗饸饹面,给个神仙也不换

细如米粉的饸饹面根根不黏、根根不断,在锅里打转
割饸饹也有多种方法。日常人们大多用厨刀割,有的用柳叶刀割,有的用筷子割,还有甚者全然不顾下面滚汤冒出的蒸汽,干脆用手一抹,饸饹就利利索索入锅了。专司看锅的那位,用柳条棍拨拉着锅中的饸饹,以确保细如米粉的饸饹面根根不黏、根根不断,待饸饹在锅里打几个转,成色一到,就将饸饹面捞入盛满凉水的缸里泡凉,再一窝一窝地晾在木制的笼屉上。
饸饹面的臊子主要由猪肉丝、酥肉、金针、炸豆腐、海带丝、鸡蛋、菠菜等食材加工调配而成。厨房的大师傅早已将做臊子的主料和佐料备齐,炉子旁支着一张四方大桌,桌上齐齐整整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调料碗,大约有花椒、大料、碱面、细盐、姜末、葱丝、菠菜叶和嫩茎,另备酱油、胡椒粉、香油。霍州本地正宗的饸饹浇的是卤,卤的关键在于酱色和糖色。
炒酱色时首先将甜面酱混进油里慢慢加热,翻来覆去地搅拌,使水分蒸发。大师傅聚精会神,一手端着炒瓢,一手执炒勺,油太热时将瓢举高离火,油温降后复置于火,不得有半点疏忽,甜面酱由糊状结成饼状,再搅开,加热,饼状甜面酱渐渐变干,颜色也就由淡黄成了深黄,待暗成咖啡色时,酱色独有的酱香味儿就飘荡出来了。届时,将油控尽,掺入半盆热水,一阵翻涌,酱色炒成。炒酱色是慢工,要有耐心,欠了摆脱不了酱味,过了则发苦。
炒糖色也是个细活儿,更需耐心。师傅把雪白的绵糖放入炒瓢,热至发黄、发红、发黑。当然,如果单论炒,若时间短,用火猛,一会就成黑的了,且味苦涩,完全不能用。负责任的师傅通常会慢火细研,反复加热降温,炒至将成黑色之时,会冒出浓浓的烟,烟势很急,这时最要紧的是放烟,新手一见就慌,老师傅则将黏稠的糖色高高舀起,徐徐淋下,再舀起,再淋下,反反复复,最后再淋下时,糖色细若发丝。这时再加一盆水,就见满炒瓢翻滚着近乎黑色的暗红汤汁。三斤白糖,要炒两个多小时,老师傅炒糖色,向来如此,从不惜时惜工。
霍州的师傅称炒酱色和糖色为“收色”。这个“收”字极确切,酱色也好,糖色也罢,整个过程从零散到凝聚,逐渐变化,控制有度。
不一会儿,炉火正炽,三四口大锅的水开了,一团团的白气翻腾上涌。这时,师傅像抓药一般,将炖得软烂的、指甲盖大小的红烧肉薄片连着汤舀进锅里,再放海带丝、酥肉片、金针菇,最后放调料,再舀一勺稀释了的淀粉汁入锅,汁入锅后须不停地搅动。接下来就是配色了,酱色糖色入锅,颜色大变,香味扑鼻而来,只见汤锅缓缓涌动,有人递过搅匀了的十多个鸡蛋,师傅一勺一勺地漂进锅里,这就看“道行”了,水沸过头,蛋花散了;水不开,蛋花沉了。唯恰如其分的是一锅卤吃到最后,仍见蛋花荡漾。师傅示意,又有人将切成丝或丁的炸豆腐下锅,又有人撒一层菠菜、葱丝,师傅就撒胡椒面,淋少许香油,放一小勺酱油。师傅潇洒地挺立在一排炉灶前,利利落落地煎炸煮炒,精细的手工制作中蕴含了师傅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、赓续不断的责任担当和对这个行业的敬畏之心。
要开饭了!饸饹重新入锅加热,再捞进一只大盆里,这叫汤锅,汤锅中需加入调料、菠菜、葱丝等。这时,浇卤的师傅被一圈碗围着,不紧不慢、一勺一碗地加臊子。浇卤也有学问,师傅的勺必须一直在锅的一个边上舀,只有这样舀到锅底,这臊子还是稠稠的、亮亮的。若是满锅舀,再好的卤,也搅成了稀汤。这些酱料由各种香料和秘制调料慢炖而成,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饸饹面的汤汁和酱料完美结合,每一口都充满了层次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。
饸饹做好后可以加入不同的小菜,小菜依时季不同花样不同,可以是胡萝卜丝、凉拌白菜,还可以是老咸菜、豆腐乳,再备上醋和油泼辣子,随食客口味自取。
开饭的场所就在院子里,满院的人说说笑笑,你一碗我一碗。这热气腾腾的饸饹充满了舒心快意和红火热闹,农家人要的就是这个人情、人缘和人气,那浓浓的乡情与亲情也热气腾腾地荡漾开来。
做一次饸饹往往需要众人一早上的劳碌,虽然有些琐碎,但这种传统早已融入乡土中,这就是礼法,其中渗透着浓浓的人情、乡情。手艺好的厨师大多为情面而奔波,乡里乡亲的,提条烟,喝壶酒,算是酬谢。他们用自己方正和勤谨的品质获得了乡亲的尊重,因此,那些厨师在四邻八舍中都有着极高的威信。
谁家“过事”了,谁家就成了一村的中心,远在城里的兄弟都得回来,长长的饸饹好似村里人的精神纽带。回来吧!一定要回来的!你可以不吃饸饹,但你不能不压饸饹,你可以不压饸饹,但你必须到场。你要紧紧地围在那口大锅前,后背寒气凛冽,面前烈焰炎炎,腾腾的烟团冲向高天,一阵风来,烟团消散,灶旁的孩童弟兄,越挤越紧。此时此刻,没有个别和孤独,只有群体与融合,没有做生意做学问的,更没有做吏做官的,你和大伙神神地侃上一阵,野野地吃上一顿,甚至你什么话也不用说,也能开怀大笑一场。一碗饸饹,悠长悠长的,记载着乡俗人情;筋道筋道的,凝结着淳风厚恩。哪一天,如果你觉得人心不古了,就想想“礼失求诸野”的教诲,这时你再回到乡下,有幸逢着吃饸饹,便添上一把劲,出上一身汗,深深吐纳几口田野的空气,或许心胸就宽敞了。
老人过世了,当然也用饸饹招待。
据说,一翁垂垂老矣,弥留之际,对来看他的老友笑了笑说:“你先吃我的饸饹了!”一派“生老病死,时至则行”的淡定。
然而,这毕竟是悲事。虽然压饸饹的仍尽力地压饸饹,师傅们尽心做臊子,可大伙总是说不甚可口。什么原因呢?师傅们这样说,一是心境所致,愁云惨淡,月冷星寒,即使只是来帮忙的人,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,便是山珍海味也着实难以下咽;二是环境使然,遇喜事,厨房门楣上的横批曰:“清香美味”,丧事则曰:“食旨不甘”。
这就是饸饹,一顿有一顿的意思,一顿有一顿的寄托。
除了大事上吃的臊子饸饹,还有一种农家平时吃得最多的,叫“花臊子饸饹”,花臊子饸饹宜在夏秋去吃,这两个季节里,田里蔬菜要什么有什么,样样数数,长得正旺,摘一把碧绿的豆角,洗个水灵灵的西葫芦,刨颗嫩纯纯的土豆,拔条脆生生的萝卜,再割块娇滴滴的豆腐,或片或丁,添海带丝、小酥肉、炸豆腐,肉是五花肉,炖得软烂,酱色也是必不可少的!此外,还有一特色,炸霍州老黑酱作味,一小匙黑酱加入,炒瓢中加热至将焦时,放薄蒜片和食油,稀释酱的过程亦即煎蒜的过程,油热、蒜熟、酱润,添水成汤,香味喷薄而出,花臊子饸饹不勾芡,色艳汤浓,吃来利口。
还有一吃法,谓“干面饸饹”,可以说是霍州快餐。大街小巷,因陋就简,有门面的,门面却也不大,支六七张桌子,有的干脆就地撑布帐,小桌矮凳,干干净净。干面饸饹较办红白事的打卤面饸饹要细得多,熟油凉拌,备于大盘,汤锅极简,但务必用酱色出味,糖色调色,入料后撒入葱花、菠菜。食客来了,抓大半碗饸饹入锅,碗底衬绿豆芽、萝卜丝、豆角丁不一,于汤锅中温一小把炸豆腐。此时,饸饹已热,挑于碗,浇汤,滗去,再浇,再滗,至碗底衬菜热了,浇汤可食。干面饸饹讲究的是汤清面香,其小料必备红油辣子。小摊上,备饼子、麻花、茶叶蛋,任食客点取。利索的师傅,两三分钟可做成一大碗。这种吃法,热面一定要恰到好处,忌不热,勿绵软。汤锅呢,仍得老老实实地炒酱。时下有的小摊,加芝麻粉,淋酱油,撒味精,吃起来总不地道。干面饸饹一般作为早餐和午餐食用,果腹好,品味也好,吃一碗是一碗。干面饸饹能凉拌,凉吃多在盛夏,叫“凉面饸饹”。凉面饸饹拌菜多为黄瓜丝、豆角丝、绿豆芽和淖熟的茴子白,调味盐末、辣子、香油、醋即可。有人也喜加蒜末或芥末,其味锋利,一下子冲击了凉面饸饹的清香。干面饸饹在和面时加碱略重,微黄,凉吃不伤胃,还泛着淡淡的碱香。
民以食为天,从茹毛饮血到食不厌精,人类一直在追求色香味的极致。一碗热腾腾的饸饹端上来,老的食客总是试图寻找多年前的味道,找到了,欣然,没有找到,怅然。或许,这就是传统的魅力,不一定最美,但总令人回味。追求传统的师傅们,凭着禀赋与坚守,尽力将其延续着。无论怎样演变,传统饸饹面能走到今天凭借的是其无与伦比的定力,单是饸饹所产生的那种强大气场,也断非文文雅雅的宴席能比得上的。过去“一方有事,四方帮忙”的厚道与对子孙的熏陶教化,直到今天,还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饸饹热闹和温暖了一个年代。不论时代如何更迭,婚丧嫁娶宴席或者仪式发生了多少变化,饸饹面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经典元素。
拼的就是真材实料,讲的就是工序不减。在霍州,饸饹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,也是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。饸饹面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和烦琐的装饰,它以朴实的口感和诚挚的味道征服了人们的味蕾。
饸饹面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更是山西霍州文化与传统的体现。它凝聚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人文,传承了几代人的智慧和热情。每一碗饸饹面都是一段故事,讲述着霍州人民勤劳、朴实的生活态度;每一碗饸饹面都是一种情感记忆,承载着霍州人民热情、友善的美好德行;每一口饸饹面都是一场味觉盛宴,让人回味无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