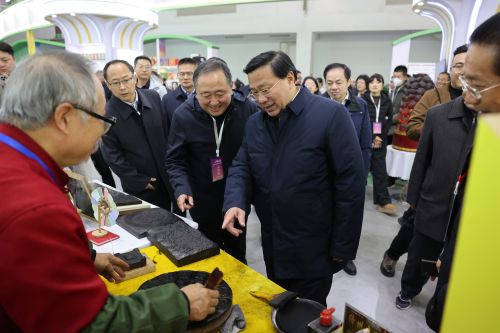饱经沧桑的家门
我这棵“树”,刚在异乡扎了根,却陡然想归家,翌日便不假思索地飞奔回乡。
我离开那年才九岁,被母亲的一个糖果诱去了镇里念书。印象里,家乡路边没有候车的牌子,也没有固定的候车点,车经过时,只要人在路边招招手,司机就会停下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,我们就站在路边等班车,一旁是没过小腿的枯黄草丛,大包小包的行李堆放在脚边,我伸长脖颈张望着,盼着班车如期到来。然而迎面而来的只有一两辆摩托,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飞驰而过,留下灰色的烟雾。这样的画面长久地镌刻在我脑海。
如今,我坐着崭新的班车一路畅通无阻,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刚下车,目光所及之处,焕然一新。原来那个杂草丛生的候车点矗立着一个候车亭,亭子颇为讲究,里外都贴了瓷砖,就连供乘客歇脚的石椅也不例外,亭子一旁还立着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,上面标注着站点名。

古榕树
候车亭不远处就是村口,村口的这座牌坊,年深日久,在长年的日晒雨淋下,变得格外沧桑,但仍可窥见其昔日辉煌,坊上飞檐画壁,两侧镌刻着些许文字,牌匾上三个大字:环下村。牌坊如同一个守护者,在这片土地,任劳任怨,历经风吹雨打也始终挺立,守护着这个安静的村落。它缄默着,一言不发,又仿佛说了许多。
走过牌坊,便是看似蜿蜒无尽的公路,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七月初,稻谷已经割了大半,日头渐毒,田间早已不见人影,只有黑黝黝的机器停在田里,不再轰鸣。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摩托佬,只得靠一双脚去丈量回家的路。我一边走,一边在脑海里回想村子的旧貌,忆起许多尘封的往事。这条路,当它还是坑坑洼洼的泥路时,我走过无数次。儿时,每至初一、十五,奶奶家地里没活,就会带着我去趁墟(赶集)。墟离村子约莫五千米,我一路兴冲冲地跟在奶奶身后。在乡间小路上,总会出现这样的画面:一群老婆婆携着几个孩童,或戴着草帽,或撑着伞,捏着袋,一路聊着家常。不用想,她们肯定是去趁墟(赶集)。同样是在这条路,有次我们咬着冰棍从墟街出来,路经小桥,看到二叔在桥下电鱼,我们三两下嚼完碎冰,脱了鞋下去帮忙拉渔网。几个人笑嘻嘻地拉扯着渔网,把捕到的鱼扔进桶里,心想晚饭肯定又是全鱼宴。捕鱼后,看路旁葫芦花开了一片,折下几枝,揣着兜里,一路颠簸着回去。
咀嚼着往事,我只身走了将近半个钟头,汗流浃背。隔着日光与尘土,我看到了路旁那几棵粗壮的古榕树,宛如一位和蔼的老者,拄着拐杖,遥遥地向我投来慈爱的目光。我怀揣着沉甸甸的思绪,三步并作两步,连忙迎上前。
儿时,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树下掷石子、跳房子,抑或是揪着榕须编辫子。那些充斥着欢声笑语的日子转瞬即逝,让人不禁感叹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。”
如今,古榕树旁不再是一间简陋的矮房,而是平地拔起的一栋用瓷砖和玻璃碎片建成的二层楼房,顶处镶着几个明红大字:环下村委会。路过大门敞开的村委会,还能看到几个干部衣着整洁,坐在大厅桌椅前勾勾写写。其中一位抬起头来,见我提着一个行李箱,诧异了几秒,随即笑容满面道:“回来啦?”我点点头,尴尬一笑,再多的话,我也说不出了。离家多年,如今你问我村主任是哪位,干部几位,我只能摇头,全然不知。
绕过村委,走过一片稀疏的竹林,可以看到一个方正的垃圾池,旁边竖着“垃圾不乱扔”的蓝牌。走过垃圾池,道路周遭的房子便逐渐多了起来。路是平整的灰色水泥路,房屋是高矮不一的各色瓷砖房。多年未归,这座坐落在山脚下的小村庄已然焕然一新。昔日摇摇欲坠的黄泥矮屋和坑坑洼洼的泥路大多已不复存在,三五层高的洋房如黑白棋子密布在这青山绿水的棋盘上,沧海桑田,不过如此。路经一两间新屋,只见院中有五六棵果树守着崭新又空荡荡的家,三两蓬头小儿在墙根下嬉戏打闹,见我皆缩头躲避。我内心油然而生一种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悲戚与苍凉。我本该明白的,当我踏上异乡土地的那一刻,从此故乡是异乡,异乡仍是异乡。天地之大,我只是一只孤鸿,一片浮萍。等我再归来,我就不再是归人,而是过客。
村中心的古树下是最热闹的地儿。常年有小贩在此摆摊做生意,或卖些时令水果,或卖蔬菜熟食。全是别的村子的老妪、老翁,蹬着一辆破三轮车,咿咿呀呀地踩到环下村。我们村人最多,稍富裕些。有的老人年迈,家里田地丢荒,只能来古树下买菜。我小时候也爱来古树下,看着小贩卖爆米花、鸡米棒、酸芒果和麦芽糖等,嘴馋得不行,围着摊位走来走去,奈何家里大人过分管束,当时的我身上摸不出一角五分钱。为此,我们几个人还商量着去捡瓶子,先是绕着村子“扫荡”,后又厚脸皮地跑去隔壁几个村子,专往屋前果树和竹林里钻,多的时候一天能捡二十来个,少的时候就空手而归。又听说卖铁赚钱多,不知谁从家里顺了块磁石出来,绑上绳子,牵着磁石四处吸铁,攒够了,我们就等着卖货郎来村子吆喝,哗啦啦一群人扛出去让他称,得了几毛钱就欣喜若狂,撒腿就往小卖部跑去。那些年,长长的白色冰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冰棍,往后吃的冰棍和雪糕都稍显逊色。
古树的不远处,有个狭小的小卖部,门口简陋地搭了个棚。棚下三三两两坐着老妪、老翁,或划摊,或打牌,或下棋,若无事可做,就凑在一处聊些家长里短,一旦话匣子打开,任是谁路过都会成为话题中心。我路过时,有位老媪抬头看我,眯着眼,艰难地从记忆里搜刮着似曾相识的名字,良久,才睁开浑浊的眼,惊喜地认出我是陈某家的孙子,又道出我父名何。

阳光从树叶缝里泄下
我与她们寒暄一番,然后依着印象踉踉跄跄地拐回了自家院子。这是我的家,一个院子和一座斑驳的房子。我在此出生,爬地,迈步,奔跑……这里的每一寸、每一隅,都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这面墙,我和爷爷栽种的葡萄藤曾攀爬过,我埋下的毛桃核曾在墙上依靠过,留下一滩滩青苔色的印渍;这棵黄皮树,我们尝过它果实的酸甜,也曾被它的绿荫拂去暑气;这个角落,堆放过我和奶奶背回来的柴火……我的童稚岁月尽数挥霍在这片小天地,爬树,摘果,摸鱼,寻虫,山林野岭哪一处不曾见识过我的无忧无虑?而今回首,方知白衣苍狗,世事变迁。
十几岁时读《十五从军征》,读到情深处,总被幻想的凄凉画面恐吓,泪如雨下。而今,我才惊觉那些年的泪穿越十几年的时空,如同子弹贯穿我的额头。如今,故乡的家,空作遮风避雨之用,旧人不在,屋内灰尘厚积;屋外,偌大的院子杂草丛生,几株瘦弱的果树倒是枝繁叶茂,一面白墙爬满黛青野藤,生锈的铁锁正挣扎着脱落。我摸遍了口袋,才想起早已没了老家的钥匙。拂去木门上的灰尘,我拍了拍衣衫,去邻家乞瓢凉水解渴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