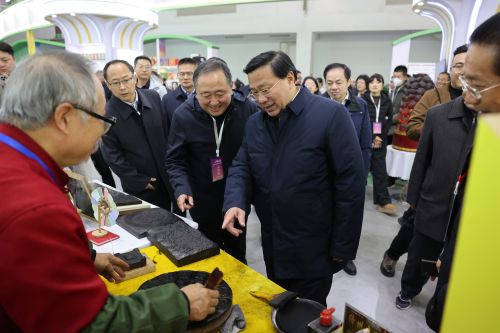我穿过乔家大院高耸冷峻的深宅高墙,却猛地与大红灯笼与斑驳伞影撞了个满怀。抬头望去,是精致而空无一人的舞楼,天井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五彩油伞。
乔家大院的这座舞楼过于美艳,以至于叫人惊异那些曾经的舞戏傩语,许是在几百年后的寒冬里仍在上演。
乔致庸和乔家的那段往事可比戏台上铿锵的梆子来得精彩。从长兄病故、弃学从商的窘迫,到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的阔绰,乔致庸的一生,偶尔光鲜亮丽,时常险象环生,总有波澜壮阔。
那个时候,乔家就风风光光地站在舞台正中央,享受着一个时代能够给予的无数灯光的照耀、喝彩的围绕。乔家的风光本无需确证,从这大院313间房的规模即可窥见那份“皇家有故宫,民宅看乔家”的辉煌。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说:“北京有故宫,西安有兵马俑,祁县有民宅千处。”而乔家大院,无疑是祁县民宅中的佼佼者。
这是每一个踏入乔家大院的游人最直观的感受与冲击。余秋雨在《抱愧山西》中这样描述道:“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,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、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,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。”但乔家大院独特的气质透露出的那一种浑然天地间的闯劲,又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诸多园林大院不尽相同:“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,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。因此,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、腐朽感或诡秘感,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。”
这里不是消化奢靡的沟渠,这里是扬帆远航的港湾。
乔家拓业者乔贵发于乾隆初年(1736)只身走西口,创设了广盛公字号。乔贵发的三个儿子均秉承先祖遗志,搏击风浪于商海,竹杖芒鞋攀古道,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。当时的大清,外有蛮夷入侵,内有太平天国。国家危难之际,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慷慨解囊,资助建立北洋水师,成为当时晋商的表率。再加上与高官政要的交好,以及重义轻利的口碑,乔家很快风生水起,银庄生意蒸蒸日上,并将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,成为包头市面上头号大买卖。
那个匆忙提上包裹踏出门槛的小伙子无论如何都没想到,自己无意间种下的一颗种子,竟会成长为一座城市、一处文明参天的文化枝冠吧!
然而成败似晨霜寒露,往往同时偎在一片叶子的两面。风光一时的乔致庸竟无一子成器。他们有的心狠手辣,有的过于圆滑,有的呆板木讷,有的甚至违背家训抽起了大烟。六个儿子中,有五个英年早逝,先于乔致庸而去,仅第三子为他养老送终。
乔致庸故后,其孙乔映霞成了乔家接班人,于民国十年(1921)扩建了乔家大院。他恪守重义之责,以银庄之力抗下货币贬值,以避免客户蒙遭损失。可义字一方,挡不住滚滚洪流的利刃,扎在乔家商号的基业上,捅了个巨大的窟窿。举目四望,还是一样的内忧外患,可这次的动荡不再提供复兴家业的机会,而是给了乔家重重一击。诺大的家业终究没能守住。再之后,这方深宅大院也难以保全,最终易了主。
乔家大院的易主,是很少有人愿意提及的往事。乔家人不愿提及,他们大多已迁至“大城市”,主要是沿海城市,有的去了国外。陈年过往如锁链,断了裂了,便不再愿意回想。媒体人不愿提及,因为这其中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疙疙瘩瘩。偶尔回来的乔家人,熟悉的深深高墙化成一张四四方方的彩色门票。有的后代双腿跨坐在板凳上,摆上些零碎特产,在曾经吞吐万金的深宅大院前做些最小的买卖。更多的人只能如我这般对着这诺大的舞楼发呆,感叹世事无常,镜月圆缺。
当如今的乔家后人驻足门廊之间,遥望深深庭院里透出的一丝古意与冷落,还能体会到几百年前发生在祖先身上的辉煌故事吗?
三宝院东厢房正中顶端悬挂着乔家大院一宝,那是最早的“监控探头”,叫“万人球”。无论你立于房间何处,均可被球面的反射捕捉到,置于许多双眼镜的注视之下。而当我抬头仰望它,浑圆锃亮的球体映出那个走西口的少年,无数进进出出的商服银票和无数翻转腾挪的过往。
一座院,就是一台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