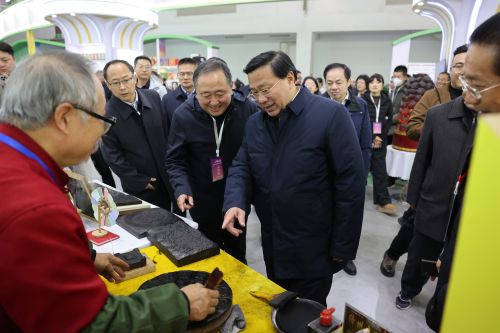新鲜出炉的金黄块垒
农村出身的人,打小是吃粗粮长大的。尤其是父母及以上几代人,在困难时期,吃糠麸、挖野菜、捋树叶、剥榆皮也是常有的事。没有精米细面,每天能吃到棒子面糊糊、块垒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。假如是缺粮户,连这棒子面儿也是稀缺的。
家长教育孩子时有句口禅:“不好好学习,将来你连糊糊、块垒也吃不开。”看看,糊糊、块垒已经成了一个人穷困潦倒时最无奈的落魄标配了。
真的是落魄无奈的日常饮食?我看也未必。困难时期,块垒是玉米面儿的,或者是高粱面的,面磨得很粗,通常情况下是搅的块垒,不是蒸的。块垒圪蛋个儿大,少盐缺油,也不再炒,又粗又涩,又干又硬,咽的时候还喇喉咙。
主妇们在搅块垒的时候常常另熬一锅玉米稀糊糊。一碗块垒,就着一碗玉米糊糊,一口干的一口湿的,或者是干脆把块垒泡到糊糊里面一起吃,呼噜呼噜三下两下,一碗就下到肚里。嚼得有劲,吃得痛快,咽着夯实,下肚饱满。从来没有感觉它难吃,反而觉得,咋吃起来这么香?
实践证明,糊糊和块垒是最完美的搭档。
那时候,玉米面庄户饭,也不是太充足,还要经常饿肚子。劳力少的,人口多的,经常是缺粮户,分到的粮食也多是发了霉的玉米。因此,春季挑苦菜、捋榆钱,秋收后捡玉米棒、刨山药,想尽办法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。
70年代末80年代初,上小学的时候,我每天裤兜里能装半口袋炒块垒去上学,那已经是很奢侈的零食了,从来不敢奢望能装半口袋炒黑豆去上学。黑豆金贵,要留到过年换豆腐吃。
那时候盼着我妈把块垒搅得颗粒大大的,吃饭的时候把最大的最硬的圪蛋捡出来,上学走的时候把它装到裤兜里。左手一颗,右手一颗,走三步往嘴里丢一颗,一边吃一边蹦跶,一路走一路快活着。如果天天能有零食,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童年的愿望就这么简单,就这么容易满足,童年的快乐就是半裤兜的块垒蛋儿。

黄澄澄的块垒
长大了,结婚了,生活好了,现在自己是主妇,做的全是白米白面的饭,却不会做一顿搅块垒,颇觉汗颜。有时,突然就想吃一顿妈妈搅的玉米面块垒,或者是玉米面拿糕。回了娘家,必点的菜谱里面,必定有一顿块垒,有一顿拿糕。
每年正月去娘家,我妈把年前置办的年货全部搬出来,炖排骨,烧鲤鱼,涮羊肉,包饺子,炸油糕……每天大鱼大肉吃着,过着地主婆一样的生活。说句不好听的,吃得多了见了这些就像见了仇敌一样,我只能笑着跟母亲说:“妈,这些好吃的您留着和我爹吃吧,给我做一顿搅块垒吧。”
我妈一愣,一边嗔怪我,一边笑着说:“才吃了几天饱饭,见过多少山珍海味,就想要这些受苦饭?我知道你喜欢吃块垒,大过年的,油水大了,吃点儿粗粮刮刮油也好。还是咱这庄户饭养人。”
于是,她把从冰箱里倒腾出来的东西又倒腾回去,收拾着做搅块垒。
粗茶淡饭保健康,时代变了,肥油大肉吃得都成了富贵病。粗粮富含膳食纤维,既降三高,又可控制体重、防治便秘,还降控癌症的发生和发展,俨然已经成为新的饮食时尚,纯天然无添加绿色古法制作的农家饭,早已上了城里饭店的热销排行榜。
块垒已经不再用粗糙的玉米面、高粱面做了,即使是纯玉米面,也是磨得非常细的精玉米面。把去皮的土豆切成蚕豆大小碎方块儿,倒入锅,用水淹住它,水不宜太多,淹没土豆块即可。待土豆块煮到七八成熟,把莜面或玉米面轻轻地蒙在土豆碎块上,让开水冲破干面。水与面的比例,以面全蒙住水为宜。面粉在锅里遇水成团,开始用筷子搅,渐渐地分离成一个个小颗粒,或者包裹了薯块,或者自成一体,大小不一,形状各异。有经验的主妇总能把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,不干不湿,不粘不沙。
搅块垒、搅拿糕,重点在一个“搅”上,但搅的方向不同,搅得方法不同,搅得力度不同。搅块垒是用筷子左右扒拉,轻轻地、均匀地、柔情地,像团弄一个小毛球,把面裹到土豆碎块上,或者自身抟成一个小颗粒。而搅拿糕是用筷子以逆时针方向甩开膀子缠,一圈一圈,搅得越来越费劲,直到拿糕又软又顽又筋,一拉筷子,颤颤巍巍地跟着就上来了,那才搅好了。再换成小火焖一会儿,就熟了。
要想让块垒看着好吃着香,有一个秘诀在“炒”,炒块垒的秘诀在“油”,油的秘诀在炸的“葱花”。油是暗橙青涟的胡麻油,葱是白长叶绿的羊角葱。铁锅上火靠热,勺头接一股清油,翻勺入锅,细沫渐浓,及等沫散,略有清烟,掌中一把葱花愉快地跳跃进热油里。
“嚓——”,花花们大声地叫嚷着,翻几个跟头,“嗞啦嗞啦”争先恐后地把胡麻油香味送进鼻子里,又从窗缝门帘底下撒欢儿似的钻到外面。搅好的块垒早已按捺不住了,急着翻个身跳了进去,热油给它们很快穿上一件金黄的外衣。
慢火焙着,换个方向,露出底下红黄的焦皮。撒点盐,来点味精,再换个姿势,外焦里软,油皮香脆无比,像一块块干干脆脆的锅巴。锅铲上下翻转,香味儿铺天盖地扑面而来。旁边的眼晴,一直牢牢地盯着,喉咙早咽了无数次口水。
吃块垒当然少不了它的黄金搭档——糊糊。一种是有米的玉米面糊糊,另一种是无米的玉米面糊糊,俗称没米糊糊,更绝的是有一种经过发酵的酸糊糊,俗称酸饭。
酸饭是把老酵母在稀释的面水里发酵后,熬进稀饭里,每次熬的时候剩下一点,称之为酸根,以便下次再发酵。有人喜欢加点糖或糖精,就成了酸酸甜甜的可口酸饭。有的地方用糜子米发酵来熬酸米粥,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酸饭富含有乳酸菌,生津止渴,消食健胃,清凉泻火,口感极好。
70年代中期,有许多种稻子的部队在雁北神头这一带驻扎,部队没有宿舍,官兵们全部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。外地人不能理解当地老百姓为啥早上一顿酸饭,晚上又一顿酸饭?下地前喝一通酸饭,下地回来又喝一通凉酸饭?
他们刚来时,有天房东大娘让住院儿的解放军小哥喝一碗酸饭解解渴。小兵哥接过碗喝了一口,咧着嘴说:
“大娘,这饭坏了,发馊了,臭得不能吃了。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从此,官兵们都把酸饭叫“臭饭”。
后来这臭饭渐渐地喝惯了,喝上以后觉得肚里边特别的舒服,又养胃又解渴,反而喝上了瘾,天天嚷着要喝大娘的臭饭。
吃块垒的另一个黄金搭档是咸菜,最好是烂腌菜。细丝茴白,宽擦萝卜,芥菜芹菜红辣椒,剥皮大蒜整花椒,一层盐一层菜,层层压实直到出水,灌熟水,压青石,高梁刷子勤打菜,腌菜脆,盐水清,放上二年不长白。这样的烂腌菜夹上一大碗,胡麻油炝麻麻花一调,一大碗块垒拌上咸菜,一大碗糊糊半温不凉,那吃的哪还有一个饱?
另一种块垒是蒸块垒,蒸熟以后再用胡麻油炝葱花来炒。把土豆去皮洗净,加水煮七分熟,用筷子能插进土豆,就煮好了。出锅晾到不烫手,用大宽擦子擦成丝(细擦容易粘成一大块),在熟土豆丝里加适量的莜面拌均匀,用手轻轻揉搓成碎颗粒。土豆与莜面比例大约为3:2,面越多越不易粘,熟后越硬。铺好笼布把莜面块垒铺进去,蒸约15分钟即熟。炒锅里倒入胡麻油适量,放入葱、蒜、花椒面煸出奇香,然后倒入蒸好的块垒,炒至金黄,搁点盐,放点鸡精,一道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“块垒”就做好了。
块垒一上,满屋飘香。这种块垒颗粒均匀细小,犹如一粒粒金黄油亮的豆豆。口感绵软,吃起来清香满口,嚼起来柔韧爽利。软中有硬,硬中有脆,就着咸菜,搭上一碗糊糊,是永远吃不腻的美味。块垒捣蒜,吃个没完,如果不嫌有口气,再来几瓣牙捣蒜,那才叫个绝!
块垒是山西民间特色食品之一,主要分布在原雁北地区一带。塞北盛产小杂粮,块垒是以杂粮为主的风味主食,有莜面、玉米面、高梁面之分。由于形状是一块一块的,所以叫块垒。“块垒”的历史至少可上推至宋元时期。块垒亦作块礨、块磊,泛指郁积之物。作为食物,“酷累、块垒”又称“不烂”,也就是“拌”的分音。因用擦子擦成丝状再拌面,有地方又称其为“嚓嚓”。
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,块垒是粗粮,是因为缺少大米白面等细粮,没办法才吃的。所以,总认为块垒是一种上不了台面的传统庄户人家常饭。但看似普通的吃食,飘出来的却是浓浓的乡土气息,凝聚的是劳动人民满满的智慧,这味道早已驻在每个人的回忆里,驻在回不去的乡愁里。
庄户人饭菜,就是这么地道。一锅两碗,半苗大葱,一盘咸菜,三瓣大蒜,盘腿上炕,伸手抓握。块垒糊糊,莜面饨饨,拨股鱼鱼,拿糕窝窝,酸菜盐汤,养胃养人,好不快活。
庄户人,没有太多的奢求,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几亩薄田,农闲打工,孩子上大学,老婆热炕头,足矣。简单的生活,简单的追求,简单的寻觅,简单的一生。
生活,就是这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