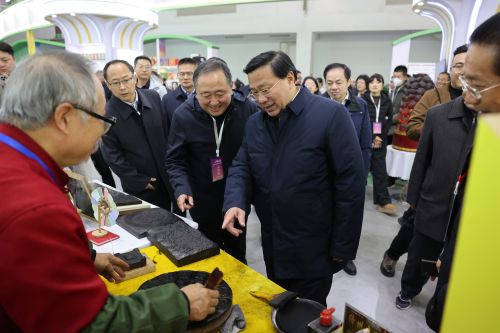藏在野草里的残碑
必须承认,我来晚了。
相隔不过十几公里,这么多年,多少次来回路过,竟从未有机缘相识,更没有深入去了解这里有个传奇人物和他故里的变迁。仓促而汗颜,就是这种感觉。站在伯虞村北口崭新的伯益塑像下,看过西面文化墙上图文并茂的业绩;手缓缓摸过被时光啃噬,被弹孔敲凹的明清民居墙壁;在一块残碑上读到那段岁月,在一片金黄的麦地里回望一段残缺而静默的城墙,这种感觉始终跟着我,如同此时灼热的阳光侵覆在身上。
村庄并没有因此而怪罪我,来多晚都不算晚,时间之水不会因我而停顿,在我认识之时历史又延长了一段而已。他是慈悲和宽容的,正如每条路最终都有明确的指向和终点。现在,他微笑着,拿起一块古老的旧砖,轻轻放在缺口上,为我铺平了这条路。
拨开矮墙下葳蕤的野草,食指隔着积尘,探触到一块青石,“有字!”心下一惊,急急地打盆水来,淋水, 再用笤帚扫,碑面上的阴刻楷体汉字就湿淋淋现了真形, 一行人凑跟前仔细辨认:“……大明崇祯六年十月十二日……起建西门记……生员毛……”,三百多年前的石头自己开口说了话。

乡间院落

朴拙的院墙
村委会西边的一户人家墙外,这块一尺有余的残碑跟别的石头顺着墙根整齐排列,如果不是无意中多看了一眼,不弯腰触摸,真看不出上面有字。硬化、美化过的街巷,从村中泊池辐射铺展开,民居就挂在这些线上, 像一座座长方形的灯,各自有炫目的资本。2014 年, 这里率先开通了城际公交车,和来时北面路过的丁村一样,都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模板。
晌午的阳光很快就吸走了碑上的水分,字迹又重新隐藏在灰白的凹痕里,野草也不过扭了扭身子,挣脱手的束缚,又遮挡在石头上,像未曾被人关注过那样恢复了平静。新的草旧的碑朴拙的墙,它们才是和谐共存的, 不在乎相差百年十年岁数。现在回想,这块石碑肯定是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,多难得,在对的时间终于等上追寻它的人。它孤傲与不屑,抵抗风云巨变和风剥雨蚀, 却依然渴望诉说。如同一个人睡了个饱觉,就等着这掬水,一点点冲走朝夕累叠的尘垢。抹把脸后,思路清晰了,坐下来,把彼时经历的种种悲喜一层层剥给我们看。
这块碑当初会立在哪里呢?西城门楼没有留下一点踪迹和文字记载。只有路南一段残缺不全的站立的城墙,与这块躺下的碑互证。村西口的麦田,正沐浴在一片炫目的金色里,阳光和麦穗,流淌着同样的光泽。这光也铺陈在这段城墙上。像时光雕琢的版图,凹凸不平的纹理里,看不出究竟哪一块儿是最初的显现。也许最外面的那层,已经不声不响回归了大地,这是它们最初的来路,也是最终的归宿。留下的这段是最后的坚守, 等着我们。麦子籽粒饱满,有一块地麦子已经割倒,等着主人用绳子捆了,拉进场院脱粒晾晒。我只好打开书本,学着农人,收割属于残碑和城墙的那一部分史实。
“杯土可以成山”,时任知县魏公韩劝谕各村乡绅百姓赶快修筑堡垒,各村村民齐声响应,有钱出钱有力出力,家家男子荷担挑箕,妇女小孩送食送水,体壮的妇女也加入筑墙行列。这发生在明崇祯三年,陕西流寇渡河入山西后,闯入村子明抢豪夺,搅得人心惶惶,鸡犬不宁,村村围城是当时的壮举。城墙用料主要是土,几百人分成几段,同时进行。一段几十人,各自分工协助。墙基筑实大约厚三米左右,用木制的工具搭建好框架,把湿润带粘性的黄土,倒入夯墙的模具中,用粗重的“夯”击打筑牢,到上边徐徐收窄,一直打到三丈高左右。单纯的体力劳动容易疲累,为了鼓舞干劲,就有人带领大家喊号子,唱夯墙歌。上百个淌着汗水的劳动者,四人或两人一组,一边握紧“夯”重重夯实泥土,一边跟着节奏吼唱着歌谣,他们使出全身的力量,在不断碰撞和歌唱中迸发出新的激情,这激情让他们暂时忘记了被侵扰的惊心和痛苦,忘记了日渐拮据的生活造成的阴影。歌声和号子在绕村十华里长的地界,在一段段依次耸立而起的城墙上此起彼伏,交相呼应。黄土和黄土碰撞出人与大地共同的心跳。
十月转凉,残碑上记载崇祯六年伯虞村开始动工筑建西门。“基甃以石,壁包以砖”,城门是一个村的门面, 在不误工期的前提下,处处都要设计精心,还要和别的村的城门有所区别,建筑样式要有所不同,镶嵌在门额上的字也要有深远的寓意和愿望。根据周边环境,建起东、西、南三座城门,都各有特色。东西城门都有城门楼,东城门楼有三层,高大雄伟,沿砖砌台阶登顶远眺, 可以看到东方逶迤连绵的崇山。顶层有塑神,上方悬挂一方匾额,“乔峰钟秀”四个字熠熠生辉,伯虞村属崇山的东麓乔山下的绵延之地。
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先祖伯益,东门券顶上方,一块砖雕的门额上书“古伯围”,古是远古,伯是伯益,围,指这里属伯益的封地和故里,也可以指向这座安逸的围城。人们对先祖的绩业牢记于心,没有更多的溢美之词, 心意一笔一划刻画在砖上,也刻画在心里,并高悬在头顶。用这种最庄重的方式表达对先祖的爱戴和敬意。让每个人都能仰着头走出去,按着头走回来。
宽阔雄伟的门楼上,自由的风猎猎而行,并不断把城东南角魁星楼角檐上的风铃声四处传送。这座城门楼分前后两道门,经明清时期历次整修加固,两扇厚重的城门外包有铁皮,嵌有圆形大钉。门洞内侧北边建有守门人住所。除了守门还兼巡逻防护,打更传信多有戒备。村内各条主巷也陆续建起巷门。由村民选定专人轮值, 入夜关闭,整巷即安。一座坚固的城堡大慰民心,可以睡个安稳觉。
一滴水可以直接回归大海,也可以先升为云,降为雨,再奔赴而至,它始终是用不同的形态存在着。液体尚且如此,这块残碑和城墙,以及肉眼看不到的另外的大部分,也一定还在,它们充盈着伯虞的体温和热血,用固态的质感和无形的感召,在大地上亘古守候,来这里的人,都是它的一部分。